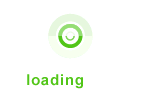东北三、四月的风,就像一个面目丑陋而又衣着华丽的女人。
华丽,是因为“她”身披春天五光十色的衣裳,并舞蹈着阳光灿烂的舞步和散发着沁人肺腑的芬芳;说“她”丑陋,是她变幻无常、出尔反尔,可以在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里,让人体味出别样的仍带着丝丝寒意的春天。
东北的大风,三月刚进就迎面向你砸来,说砸,是因为“她”来势汹汹、大大咧咧、呼天喊地,挟着东北的“她”特有的粗门大嗓,“呼拉”一下子就习卷到你的面前,抽(刮)你没商量,也没有商量的余地。然后就漫天沙土飘扬、暴土蔽日、尘嚣直上、一泻千里……在不经意间,“她”突如一个正在大怒的东北娘们(请原谅我用了这样一个粗俗的字眼)嗷嗷着噪门(那风声实在像一个嗓门憨粗的女人的声音)在斥责着她不顺眼的人或事,声嘶力竭亢锵有力,忽儿又百般妩媚柔肠百转,绕着你的脖子热“吻”有余鸟语花香……猛然,“她”又大怒起来,继续着她的高歌猛进,继续着她的喋喋不休的聒噪……没有缓步前行,没有徐徐道来,有的只是一种霸气和凶悍。此为春风之“一季”。
“她”的二季,开头来的要有些婉转添情。添情者,沙尘就如“她”的情话,时时刻刻萦绕在你的身上、脸上,这时的她,一改直来直去的脾性,一点点、一层层地热语柔息,再“哈”出一息让你晕眩的春的娇态,尤如江南三月里的细雨,点点滴滴点润着你的脸颊,不由你不迎着她自愿地让她妆抹,感恩戴德地可着劲儿地抻着脖子由她胡闹……“啪”地一下,突然之间她就变了脸,里三层外三层上上下下地就没了一丝的温情,沙呵土呵还有乱草,强行地把你的鼻子嘴捷毛拍了个“正着”,妆也得妆,不妆也得妆,爱咋咋地,那份“呵护”,直让你感到一种浓烈,一种刻骨的炽热。适才的那种小女人温柔,此时一扫无余------烈烈的意味。
当然,集前两季之“恶贯”,风中第三季才让“她”露出最可爱的春之真谛。
风女神停歇的时候,也是“她”最可爱的时候。走热了,她就“站”在那里,借一下远处贝加尔湖的凉气,轻轻地扇一下,洁白的春雪就会悄悄地落下来,洗洗城市的街道、也洗洗人们一个冬季的尘灰;跑疾了,她也会把纤细的臂膀伸向长城里处,摘一瓣江南春雨,洒向她的四周,让江南春雨变成冻雨,凉一凉刚有些燥热的、还冷乍热的大地;走累了,她就静静地站在那里,用一种平静的目光,俯视着初青的大地,此时,一道带着灼热的阳光就会烫吻着你的面颊,热遍你的周身,温热你的心田,滋润着整个还没完全解冷的大地……当然,“她”的这种安静只是短暂的那么一小会儿,很短促,但短促的安详会给人带来长长的回味,悠长的想念,于是这安详就显得华贵无比,珍贵无比,还会想着那下一次的短暂。华丽的盼望。
东北的春天是风的舞台,桀骜不羁的舞者,风风火火刚柔并进地展示着她美丽的身姿,疯颠也好,狂吼也罢,却是一种地域的风骨,恨她、宠她、爱她、想她,三个季节,三节风的个性,百种睱思,却读不透她骨中的“风”毛麟角;虽然时不时地骂着,斥责着,可我还是爱她,她的火,她的辣……有了这爱,就足够了。
------